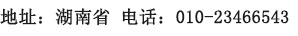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说起这双小脚,真真的让人心疼了一辈子……
“裹脚”,母亲赶上了末班车。据母亲自述,在动荡的清朝晚期,还沿袭着女人裹脚的习俗。
裹脚要从小的时候开始,在母亲十四岁那年,姥爷用剃头刀割开母亲的脚趾缝,把无名趾和小脚趾硬生生地折向脚底,然后用布裹起来。(难道,那时的人都那么的愚昧吗?不,是那个社会的愚昧和落后)
刚开始,人是无法走路的,接下来要慢慢地试着走路。可想而知,落后的社会制度,给那时的女人们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灾难!而且这种痛苦和灾难将伴随她们一生。除了肉体的伤痛,那精神上的痛苦和自卑感给她们带来的种种压力,是我们后辈人无法体味的。
自裹脚那天起,母亲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姥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偷偷地放开了母亲的裹脚布。母亲的脚后来就变成不大不小的“小脚”了。
当我看到母亲的脚时,无名趾在中脚趾的下面,二脚趾已被大脚趾和中脚趾挤起,而小脚趾已经完全在脚掌下侧卧着,生生地被踩在脚底下,把脚掌都硌出一坑。从裹脚的那一刻起,对母亲来说,人间已无平坦路……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生素食,就是过年也只吃鸡蛋或白菜馅水饺。那是因为她心里有着信仰----积德行善。
母亲懂些医道,对行针、药理药性也略知一二。
母亲为人慈善,乡里乡亲的有求必应。什么小孩拉肚、涨肚、月疴抽疯,就连大人起疙瘩、长疖子也都找她。
所以十里八村的小孩有病都愿意找她给看看,无论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因为母亲年岁大,走路不方便,大多都是赶马车来接。
特别是冬天车上铺垫厚厚的草,铺一床棉被,盖一床被,再披件皮袄。只要马车一进院,不管家里活多忙,妈妈赶紧放下手里的活上车就走。
母亲最拿手的是治小儿惊吓昏睡不醒。她有个“宝兜”,白花旗布做的抽口的小布袋,里面装二斤小米。
在被惊吓睡着的孩子头前放好一碗水,再拿一空碗,母亲把米装满空碗,拿出大手绢蒙在米碗上,用手绢兜住碗口捋到碗底,然后攥住使碗倒过来,先在孩子的头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然后翻转米碗,打开手绢,碗里的米会根据孩子惊吓的程度少去一部分。捏三捏米撒在水碗里,再从布袋里拿米,把米碗里的米补满。去孩子头上转,往返三次,当第四次打开手绢时,碗里的米已经不缺了。
这时,奇迹出现了,你通过米碗上口向阳光望去,就会发现最高时,会有四个米粒叠罗汉似地立在那里。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相信这是至今的科学无解之迷。也许是信仰给了她能量。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母亲的博爱和善举是义务的、无偿的,乡亲们都很尊敬她,母亲也在十里八村留下了相传很久的口碑。
在母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曾为她老人家写过一首小诗:
怀念我的母亲
食素修真性善人,胸怀豁达秉慈心。
宝兜尺酿灵仙药,穴道分舒解痛针。
挽救众生扶危命,施人孤寡助乡邻。
好德天养凡尘女,安度福终寿老身。
母亲不识字,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文化大革命”时不知是普查户口还是做什么,生产队会计和队委会人到我家时,才根据我舅舅的字号,吴常瑞、吴常忠,他们说这老太太会法术,就给起了吴常法的名字,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滑稽”,他们怎么想出来的呢。
父母的基因在我们的骨子里凝聚,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就这样在子孙后代中延续……
每个人都有父母,但每个人的父母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有一点“天下父母心”是一样的。
每个父母都是儿女的一部书,而每部书都有着不同的内容,儿女一生都很难读全、读懂、悟透……
母亲
娘亲德品若天书,教诲儿孙细细读。
汲取精神传血脉,行如善水性之初。
父爱如山,母爱似海!
还有句话:父爱无言,母爱无边!中华民族,古老而文明的炎黄子孙,切记百善孝为先!
作者简介:孙庆友,网名:闲弄玉箫,犁翁。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黑龙江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大庆市诗词学会理事、林甸县诗词协会副主席。有作品收录于《北国龙吟》、《流韵五国城》、《放歌凤凰山》、《华夏放歌》、《黑龙江诗词大观》等十几部诗词专集。著有《边荒犁痕》诗词集。
孙庆友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