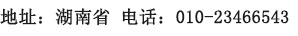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我与林甸不得不说的“五”段情缘作者李重华第一次听到“林甸”这个名字,是在年9月1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被分到班之后,听人说,我们班的班长李荣生是林甸的,但林甸什么样,在什么地理位置却一无所知。确切地说,因与我无关,也就没刻意探其究竟。后来,意外地提前离开了班级,与班级断绝了联系,更与李荣生无任何音信往来,别说林甸,就连“班长大人”也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
过了若干年后,我由呼兰师专调到大庆,不时舞文弄墨地在报纸上发表诗歌、散文,偶尔也有报道关于我出现某些文化活动的消息。有一天,《大庆日报》一位我熟识的编辑刘文兴转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寄信人叫张子龙,是林甸县畜牧局的,是问我还有没有我出版的《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这本书,他要买一本。当时,我手头已经没有了,但呼兰萧红故居有,我便回信中告知他,去呼兰萧红故居找找看。之后,再没收到张子龙的回馈信息,这件事也便“挤”到我的记忆夹层里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大庆市民政局常务副局长陈海燕,要我和他们合作出一本反映大庆市转业官兵模范事迹的报告文学集。材料由他们提供,我负责组织编写。作为大庆市写作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我,觉得重任在肩。民政局转给我的材料,大庆的五区四县都有。四县我最先想到的是林甸,因为林甸有我大学同学、老班长李荣生,有我的“粉丝”张子龙。这本报告文学集被我命名为《绿意油情》,收入3位林甸的复员转业兵:聂生彬、王宪林、张化祥。为了写好这3个转业兵,我一个一个地带着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林甸,与林甸有了一层更深一层的了解,随之,便产生了一桩又一桩难解的情缘。
?情缘一
由于《绿意油情》一书出来后,又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我再次高频率地来到林甸。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聂生彬在整理一本书稿(他的第一本著作《门》)。他提出让我帮他修改,并为他写了《序》,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著作《度》、第三本著作《朝闻夕说》、第四本著作《桥》、第五本著作《老兵道情》以及尚待出版的第六本著作《路》。这六本著作都是我写的“序”,我还以《人间万象收眼底挥洒自如任驱驰——聂生彬创作心灵轨迹素描》为题,对他的创作进行了纵横扫描,做出了综合评价,发表在了《大庆社会科学》年第3期上,扩大了聂生彬创作的社会影响。聂生彬和我成了多年的忘年交,特殊的”父子情“。他每有大事,必和我商量,这份”情缘“,难以穷尽。
?情缘二
在一次市里召开的文代会聚餐上,桌对面一位同志问我:“李重华来没来?哪位是李重华?”我问:“你不认识他呀?你找他有事吗?”他说:“我不认识他,没什么事,就想认识认识他。”我笑了,我旁边认识我的人也笑了。我说:“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人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立即向我伸出手来说:“您就是李重华呀?久仰久仰!”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董谦,林甸的。我读过您的《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写得好!早就想认识您,就是没机会。参加这个会我想您一定会来,就一直找您,可一下子找到了!”……自此,我认识了林甸的第二位朋友——董谦,真正的文学之友。年,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他的发言对我的诗歌创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评析,给与会的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8月18日,在由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大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召开的董谦小说《荒界》创作理论研讨会上,我以《荒风野俗幽默如歌》为题作了长篇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肯定。虽然现在我们的联系不是那么频繁和紧密了,但彼此在各自心中的位置是无法改变的。这份“情缘”,带着墨香。
?情缘三
那个当年我的“粉丝”张子龙,不但找到了我的著作《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而且从旧书市场花高价买到我的另一本著作——《学海飞舟——治学奇思放谈》。对于我的书,只要一出来,他就立即收藏。我最近又有一本书《文心弥情》要出版,他早早地就跟我打了招呼,我是一定要送他一本了。他每到节日,必打电话或发北京治疗白癜风去哪家医院最好哪里能治愈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