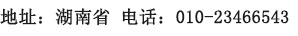年妈妈去世已经五年了,可我总觉得妈妈还活着,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妈妈慈祥的面容,尤其是每当走进妈妈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屋,习惯地招呼一声“妈”,总是使爸爸和在场的兄弟姐妹们与我一同凄然泪下……
那时,我们家穷,全靠父亲一个月四十七元的工资养活着全家九口,为了不让我们兄弟姐妹受田垅之苦,长大能有点出息,爸爸和妈妈咬着牙,先后把我们送进学校。
这一来,本就穷得要命的家就更拮据了。
家里总是吃着这顿愁下顿,今天没完愁明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哥四个(大哥在安达念高中)每顿饭每人最少能喝四大碗掺了野菜的稀粥,然后望着已经空空了的饭盆不甘心地舔净碗里最后一点残汁,恋恋地离开了饭桌。
而妈妈只是默默地收拾好碗筷,到灶间打扫点锅底充饥,或者在我们这些仿佛永远也吃不饱的儿女们对盆里锅里彻底扫荡之后,妈妈悄悄喝一碗白水,就算吃了。这些,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偶尔在饭桌上我们让妈妈也吃,妈妈总是凄然一笑说吃完了。粗心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妈妈是在用白水节省一碗两碗菜粥安慰我们那总是填不满的胃。
从我记事儿起,就没见过家里正经买过煤和烧柴。夏天,放了假的哥哥领着我和二哥到野外去割草,背回家晒干当烧柴。一天两次,天天不误,一捆柴足有五六十斤,走几十里背回家,胳膊勒破了,肩膀压肿了,疼得难受,妈妈每天含着泪加热毛巾轻轻为我们揉擦。
我们也知道妈妈的心比我们更难受,可为了艰难地活下去,却不能把我们留在家,妈妈唯一能做到的,是为我们弟兄多带上几个面菜各半的苞米面窝头,这对我们,已经是很大的奢望了。
秋天,是爸爸领着我、二哥还有妹妹顶着晨星去野外刨槎子,早饭前回到家,妈妈便为我们摆上饭桌,然后独自去把槎子上的土磕净,码成垛,再去把我们没背完的槎子背回来,一干就是大半天。
冬天,我和二哥出去捡煤渣,不知为什么,那些年的冬天特别冷,天上的星星也冻得成宿打颤。每天清晨四点,早已起床了的妈妈,便开始满含苦涩和无奈地轻轻呼唤我和二哥起床,于是,我和二哥就穿着妈妈为我们百纳千针缝补的陈旧但决不破烂的棉衣,冒着奇寒出去了。
昏暗的灯光下,妈妈那瘦弱的身躯倚在门边,一直望着我们蹒跚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不论我们满筐而归还是徒劳而返,妈妈总是站在家门前等候我们,用热水给我们洗已经冻得麻木、满是裂口的手。
有一回,为争一个垃圾箱的煤核,我和二哥被另一帮孩子打了。回到家,妈妈轻轻为我们擦洗和包裹,妈妈那止不住的眼泪滴落在我和二哥的伤口上,我们的心颤抖了,真想扑在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然后说,妈,我受不了,不干了,可望着妈妈憔悴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我和二哥还是照样每天清晨四点挎起煤核筐。
有一回,我和二哥挎着煤核筐刚翻完两个垃圾箱,突然变天了,转眼间冒烟大雪搅得天昏地暗。我和二哥一下子吓懵了,当时才十岁的我紧紧抱住比我大一岁的二哥,我们死死挤在垃圾箱后面,恐惧地看着昏黄的天地,肆虐的狂风,身边越旋越多的大雪。
我颤抖着对二哥说:“二哥,完了,回不去家了。”二哥只是惶恐地说:“别怕,别怕……”,咋不怕呀,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在狂风大雪中,只有我们无助的、弱小的哥俩,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们觉得死亡就要来临。
这时,我突然发现远处风雪中有一个蹒跚的身影,而且,我分明听见一个最熟悉、最亲切的声音在急切而焦虑地呼喊我们的名字,是妈妈!没错,纵然风再狂,雪再猛,也挡不住这人世间的最强音!我们一下子扑过去大哭起来,妈妈紧紧地搂住我们,轻轻地说:“别怕,妈来了”,有了妈妈在身边,我和二哥真的不怕了。
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初中毕业,我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我和二哥,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总是拣哥哥和虽然才十六岁却为补助家里生活被迫辍学而参加工作的姐姐穿过的,经当裁缝的父亲改一改,妈妈再给我们熨得平平展展的旧衣服穿。
雷锋说过他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我们却只能说我们哥几个穿衣服是:旧三年、换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
尽管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从未感到过寒酸,只感到母爱永远在心里的踏实。念书时,作业本用完了,铅笔只剩短短一截,我们就用作业本的反面继续写,找根木棍儿把铅笔头绑上接着用。轻易不买新的,因为我们知道,管家的妈妈已经把一分钱掰成几瓣,这个家之所以还完整,大半是靠了妈妈那早已忘却了自己的无限操劳。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考上了大学、高中、中专。邻居们说,这回老王太太熬出头了。这时,我们才好像忽然发现,妈妈那斑斑白发已经掩住了妈妈的昨天,可那深深的皱纹中仍然是无尽的慈祥。
妈妈老了,可苍老了的妈妈仍然在为儿女操劳着,仍然一个月两个月舍不得买一斤肉,十天半月舍不得买一回菜,攒着每一分钱,按月汇给在外地念书的我们。每当我们放假回家,全家团圆了,妈妈还总想法做一顿好饭,也仍然在旁边满足地看我们香甜地吃,然后收拾下碗筷,去灶间吃一点残汤剩饭,从没听妈妈说过累,从没听妈妈道过苦。
记得,那年妈妈患了阑尾炎,可她一直挺着,尽管疼得脸上直冒冷汗,仍然托煤坯子。我们这些粗心的儿女还以为妈妈只是累了,就劝妈妈去歇歇,可这时,妈妈已经疼得站不起来了。
我医院,大夫说,阑尾炎已经穿孔了,再晚送几分钟就危险了,好险哪!妈妈就是这样,为别人豁出命的干活,从不计较吃什么,吃多少,我们望着病床上妈妈腊黄的脸想,假如世界上评选最伟大的女性,那一定是妈妈!
妈妈突然病了。其实并不突然,经过几十年的苦撑,耗尽了精神和心血,终于象吐尽了丝的蚕,躺倒了,妈妈病了,而且越来越重,而那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了工作,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本应该享儿女们福的妈妈却连一口汤都喝不下了。
那时,除我,二哥,四弟和老弟外,妈妈的另外三个儿女都调到外地工作了,妈妈僵卧在床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外面,只要院外有声音,妈妈就会缓缓地抬起胳膊,向院外指去,当我们只身返回来,妈妈便定定地瞅住我们,好像在问什么,我们知道妈妈是在想外地的儿女。
后来妈妈又硬让我们把她老人家扶坐起来,脸向着院外,白天黑夜就这么执拗地半卧着,浑浊的老眼始终盯着窗外,嘴里喃喃不清地叨念着哥的名字。
看着妈妈病成这样还在切切地眷念着远方的儿女,在场的人又一次哭了。那天,妈妈突然呼吸急促起来,但一刹那又停了下来,甚至心脏也不跳了,我们立刻扑上去,哭成一团。
那时,除哥哥外姐弟们都回来了。二哥摇着妈妈的臂膀嚎哭着:“妈,你不能走,我哥正在回来的路上,妈,你再等等我哥,再看看我们吧……”,我本不相信世间有魂灵,但这回我信了,因为妈妈十几分钟后忽然又恢复了心跳,并且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一定是那殷殷的母子情,促使妈妈的生命顽强的延续,哥哥终于赶回家了,妈妈无力地握住哥哥的手,两行清泪沿着妈妈瘦弱的脸颊淌下来。
这是对世界,对生活,对儿女的眷恋,我们知道,妈妈真的不愿意走啊!妈妈这最后的泪,淌碎了所有亲人的心……
妈妈的最后几天,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日夜守候在妈妈身边,哪怕就多一天,一分钟也行,可妈妈处在昏迷中,一直没有睁开眼睛,终于在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嚎啕中走了。
那是冬天一个干冷的清晨,当哥哥摔碎了民俗传下来的,但谁也说不清确切代表什么含义的丧盆,我们知道,从此,我真的永远失去了妈妈,随着灵车的开动,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是一片悲哀的空白。
灵堂里,我望着妈妈的骨灰盒,真不明白那小小的木盒,怎么就容得下妈妈那么博大的母爱,怎么就容得下妈妈那几十年的愁苦和辛劳,可不管怎么说,它却永远隔不开儿女们对妈妈那刻骨铭心的思念。
而今,我已经在社会上有了立锥之地,是有了孙子的爷爷,另六个兄弟姐妹也分别当上了县长、行长、经理、科长、校长什么的,也大半做了爷爷或奶奶,可我总是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妈妈还活着。
本文曾刊发于一九九七年林甸县文艺创作、二00一年北方文学第一期、二00六年大庆晚报母亲节专栏、曾获邯郸、齐齐哈尔、唐山、大庆等六市征文二等奖。
作者:王志武,林甸人。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