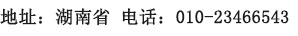题记:
跨年的最后一天,也许只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会勾起对往事的追忆。那些幼时生动的画面满脑满眼,一张张面孔既熟悉又陌生。此刻,突然发现大半生有太多的似曾相识关于月夜雷同的场景,曾经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竟然一股脑地在脑海里深处喷涌而出。在我记忆中,乡村老家的月夜魅力是独有的,也许只有走在孤独的路上更让人浮想联翩。小城故事的月夜诉说人生打拼的章节,就连标点符号都是那么的在意。乡村老家的月夜有独特的魅力,还有冬天皑皑白雪,万家灯火,又增添多少童年的回忆。我的祖辈生活在齐鲁大地,少年时短短的三年在祖籍之地,更是在梦中还在呼唤祖母,那是放夜校时,十一二岁的年纪,在我祖辈留下的用石头砌成石头院子,也许就是恐惧,其实就是恐惧后面有妖魔鬼怪,每每进院的大门,一路喊着一路奔跑着,瞬间见到祖母在油灯下摇着纺车,彼时已经是四十年前的片段。眼睛好像模糊不清,外面的冷气迅速就想给睫毛冻上冰。最快乐还是夏天依偎在祖母身边,望着美丽的星空,听祖母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每个星星祖母都能讲出故事。蛙声,知了声,还有讲不出小虫子声音!石墙上小壁虎趴着寻找蚊虫,蝙蝠飞来飞去。祖母说,蝙蝠是老鼠偷吃了盐变的。后来在初中学了生物才知道祖母讲的是传说!月夜还是让人更清醒,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时看大门的保安常说的三句话,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哲学家研究的道理走向最基层。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大智若愚吧。
七
老家夏天相当的热,越热树上的蝉叫得越欢。
每当中午是要睡午觉的。
祖母用麦秆打成一个草苫子,每个同学都是,铺在班级的空地一个挨一个。
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因天气热,中午大多都是喝汤(吃面条),老家把吃面条叫喝汤。
虽然不是纯白面的,但是感觉很好吃。
尤其是捞凉汤(面条),祖母烧开一盆水先把凉了,就是降温和凉水那般温度,然后再煮面条,把煮好的面条捞到那盆凉水里,祖母再把腌制的香椿芽拿出来,用刀在案板上切成碎末。
吃面条时,在碗里上面撒上一层,再倒上酱油醋,用筷子拌拌就吃了,每当吃面条时像坐大酒席一样那么好吃。
吃完饭就去学校,到班级开始各自铺上自己的草苫子睡觉。
有个淘气的男孩有时不愿意睡,看别人睡着了,他在别人眼皮上抹上万金油(清凉油),一会儿整个班级都被惊醒了。
实在睡不着了,几个男孩子跑到学校苹果院里偷苹果吃。因为中午天气热,老师也睡午觉,看果园的也睡午觉,趁这个机会跑到果园里摘几个苹果拿回来吃。
说起坐大席来,记得有一次去人情吃面,(吃面就是像东北生了孩子下奶喝喜酒),因为祖父是哥四个,再加上祖父的叔父下边的本家的叔叔婶婶。
去谁家都是大家凑礼份子,又是盒子,也就是过去的食盒吧,有面盒糖盒,还有给小孩做的铺的草包盖的小被布料等,那是小姑在公社上学,三叔在部队,我们这家我就是代表。
大人拉着地盘车,上边放着盒子,还有小篮子里的面糖之类吧,女人小孩子跟着走。
大席很是丰盛,开始先上四个果碟,也就是四个小蝶装着不同的糖果之类,其中就有祖母在集上偷塞到我嘴里叫粘果的。
那盘五颜六色的粘果,我吃了好几粒,四凉八热十大碗两大件。
祖父常教导,有客人或者做客吃饭,别人吃时才能吃,别人放下筷子自己放下筷子,筷子不能超出桌子,就是悬空那样,那样碰了掉地上不礼貌,再好吃的也不要连续叨。
山东把夹菜叫叨菜。
出门见到大人就说话,该叫什么就喊什么,不知道的就问问。
附近胡同那里,有个与祖母差不多大,祖母让我喊她大嫂,有时感觉不好意思。
这就是庄乡的辈分,祖母常说千年的庄乡万年的邻居。
老家的规矩特别多,前面几里路就是大汶河,往东几百里就是孔子的故乡。
祖父祖母平时把规矩告诉我,我也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至今还想起来好多,给他人倒酒,要一手提壶,一手伸出手像请,代表对他人的尊重。
满杯酒半杯茶,倒酒要倒满,倒茶不要倒满。
祖父的酒壶是锡壶,酒杯就是装三钱的酒盅子。酒也是筛热了喝,有个架,把酒壶坐上,底下应该是用酒点着,看到上面酒壶口冒热气就开始倒酒了。
来客人能够上桌子倒酒也是很荣幸的事,大多数是姑姑姑父们姨夫姨来才能上桌。
平时吃饭,三口人相依为命,我往饭屋给祖父祖母盛饭,一顿饭要跑好几趟。
饭屋的风箱挺好玩的,有时帮祖母拉风箱,夏天烧柴,冬天烧煤,呱嗒呱嗒——,感觉挺好的。
等做完饭鼻子眼里都是黑黑的。
锅台墙上贴着一张用手工制作的画,是祖母从集上买回来的。
她说这是灶王爷,灶王爷像在画上半部一个大画像,带着乌纱帽。在大画像下边三排小画像,灶王爷一家二十多口人的画像,祖母一一数落着这个那个都是灶王爷什么人,我就记住灶王爷。
后来有时家里没人,祖母还说有灶王爷二十多口给看家那。
每当腊月二十三,祖母放上供品,把那张画揭下来,然后念念有词,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用火柴把那张灶王爷画点着,灶王爷二十三就是上天去汇报了。(待续)
林甸往事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