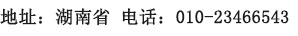见到根雕艺人栾兆明的时候,他正坐在午后的阳光里眺望着远方。举起相机的刹那,我知道那瞬间定格的不仅仅是老人八十三年的风雨人生,还有他对这片黑土地一生的眷恋。
栾老是年出生在莱芜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娃。年,山东省组织十余万青年开赴黑龙江开垦号称“北大荒”的千里沃野。年仅21岁的栾兆明就在垦荒大军之列。
栾兆明家境殷实,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正值青春热血的他响应国家号召,想趁着年轻到大东北的广阔天地里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想凭借自己的双手打造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
然而现实和梦想相差太远,当垦荒大军跋山涉水来到林甸县东兴乡的时候,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一人高的高草,人烟稀少,地多荒芜、群狼出没……
这些年轻人没有退缩:开荒种地、打井引水、盖窝棚,搭地铺……沉睡多年的黑土地热闹起来,到处都是垦荒人劳动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
秋天,一座座民房拔地而起,这些大姑娘小伙子们终于住上了新房。
后来,经人介绍,栾兆明和垦荒团里的姑娘王启兰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至此才结束和单身汉挤睡南北炕的生活。王启兰当时是妇女主任,有文化、爱劳动,还是劳动模范,经常去市里参观学习。
58年,念过五年书的栾兆明成了一名司机,唯一一台下放到东兴乡的斯大林80号成了栾兆明的工作伙伴,每天他驾驶着这台车在东兴乡负责代耕。第二年,区里建起了农机站,他被调到农机站一干就是几十年。
57岁的时候,栾老退休在家,闲来无事他开始专心起自己喜爱的根雕事业。
一天,儿子要去太康县购买收割机,邀栾老一同前往。
当时正赶上泰康县开垦一片荒地,拖拉机冒着黑烟嘶吼着从地下掘出一个个巨大的树根。栾老的惊喜不亚于发现了稀世珍宝,他发现这其中好多树根形状特别好,便和开荒人说明想法,于是一个个硕大的树根便和栾老一同回到了家乡。
说到这里,老人摘掉老花镜一本正经地和我们说起了根雕艺术:“根雕也叫根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选材。根雕用材必须选择材质坚硬、木质细腻、木性稳定、不易龟裂变形、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如黄杨、檀木、榉木、柏木、榆木等都是根艺造型的上好材质品种。而林甸县大多都是榆树树根。”
有了根源,他又购置了木雕创作的工具:锯、木锉、凿子、刻刀、扁铲、斧头、木钻、木锤、刨子等,除此之外还购买了毛刷、砂纸、绳子等。
为了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他还在书店里选择了相关书籍,茶余饭后,劳作之闲,栾老便细心研究,潜意琢磨,一时间,对根雕事业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一件作品,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甚至是更久,可是他乐不此疲,醉在其中:“你们看,”老人走到北墙的一个柜子旁指着一件根雕自豪的说:“这件根雕我雕刻了足足有半年,这四面的图案各不相同。”说着,老人转动起那件巨大的根雕,我走过去仔细地欣赏,果然如老人所言:根雕四面各不相同:一侧峰峦叠嶂,一侧楼宇阁台,一侧鸟雀栖树,一侧花绽枝头,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那峰顶平坦处,两位高僧正在悠然远眺……
看到我瞠目结舌的样子,老人笑呵呵地讲起了这件根雕的创作:“当时我雕刻完了四面的图案就觉得这山顶上缺少点什么呢?我是天天想,夜夜想,就连走路吃饭我都在琢磨。哎,终于有一天,我想起了泰山半山腰上的一件根雕,于是我立刻有了想法,那就是雕刻两个高僧远眺啊。别着急啊,我找找原图给你看看。”
栾老兴致勃勃地打开他的百宝箱,我也凑过去,那里都是多年来他收藏的根雕照片,相关书籍,还有各家报纸报道他的事迹的文章剪裁。
“你看看,这不是。”栾老指点处,泰山山顶上,一对高僧正在饮茶畅谈,神闲若鹤,悠然自得,好不自在。自古泰山有山有水,有寺有庙,山青水秀,风景如画,是家乡的山山水水赋予栾老创作的灵性,栾老的创作也融入了对家乡的无限眷恋。
一日闲游,老人偶得两个树根,甚喜携之而归,但久思不得结果。于是便又成心病,吃饭饮茶,行路劳作,心中所想都是这两个树根,到底该雕刻成什么样的作品呢?
三年后的一天,老人正在侍弄自家小园子,忽见一肥虫正卧于菜心,其首高高昂翘。栾老顿悟,灵感油然而生,这不正吻合了那两个树根的形状吗?
栾老扔下锄头,快步返回屋中,拿出工具,刻刀舞动,根屑飞扬,一气呵成,终于这对沉睡地下多年,又搁置三年的树根有了灵性和生命。一对栩栩如生的蜥蜴诞生了,一只朝天而嘶,一只深情遥望。生命总是需要慢慢成长,正如这对根雕蜥蜴,它要吸收多少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又要苦苦守候多少年才能遇到栾老这位有缘人,才能得以见天日,才能成就它生命的绝唱啊?
望着这件作品,栾老久蹙的眉头渐渐舒展,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几十年如一日,恋老倾心痴恋于他所热爱的根雕事业。在他的辛勤雕刻之下,一件件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茶几、花架、衣架一应俱全。
我流连于栾老的作品之海,畅游于艺术之间,每一件根雕作品都是栾老内心情感的结晶!巧妙的构思、精妙的手法、原木幽香、造型特异、惟妙惟肖……我赞叹不已、由衷钦佩!一件件普普通通的天然树根,通过栾老的巧妙的雕琢,有了灵性,绽放了生命,这沉睡地下的腐朽在朗朗日月下就化作了神奇。在创作的过程中,栾老享受着根雕艺术的魅力和无穷的乐趣,而他老人家也在作品中找到了自我,成就辉煌的人生。望着满屋子的作品,听着栾老娓娓地讲着根雕的历史,我感受到了栾老平凡中的伟大,更感受到了根雕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栾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您不想回去吗?山东是一个很适合养老的地方啊!”望着栾老满脸的沧桑我问道。“不回,也不想回了。”栾老平静而祥和。“为啥?毕竟落叶归根吗?”我追问。“归根?是,可是我早就把我的根扎在这儿了。你大娘她长眠在这儿了,无论生死我都得守着她。再说,儿子、闺女、孙男娣女都在这儿,我能去哪儿?哪都不去,就在这儿,这就是我的根。”栾老目光悠远地望着远方,那目光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是巍峨的泰山,是垦荒大军的滚滚人潮,是年轻时王启兰如花的笑靥、还是儿孙满堂承欢膝下,或许是,或许都不是……栾老坐在午后的阳光里,整个人都沐浴其中,那是一种别样的舒适和温暖,没有骄阳的燥热,没有落日的凄凉,暖暖地,带着晚秋的成熟与厚重,和窗外高远的天空焕然一体。我知道,栾老不单单把根扎在了林甸,为林甸的发展倾其一生,就连他的生命和血液也早已经融进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那才是他一生守候的根魂。历尽百年,时光不老,岁月的刻刀把沧桑刻满栾老的额头和眼角,如雪的韶华浸染了他的头发,黑土地的深情摧弯了他坚挺的脊背,他和所有垦荒人用满手的老茧托举起了东兴乡的繁荣和昌盛。那一刻我深深地懂得:栾老才是岁月熬进百年精雕细琢的一件最得意之作!
作者赵艳琴,林甸作家协会会员。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