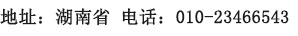昨日晚上,大姐告诉我,王建峰去世了。心里一惊,他才60岁刚出头。前几天刚听说有病,仅仅几天时间就去世了。真是让人一声叹息。半夜醒来,再无睡意,王老师的身影总是在脑海浮现。王建峰是我的小学老师。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一直担任班主任。他是“大学漏子”,高考考了很多年,最终没考上,便回村里教书。刚教书的王建峰,青色的连帮胡子,高高挑挑的个子,小眼睛里泛着光,冷冷地浅笑。总之与村里人的农民气质完全不同。有次他被我们甩着鼻涕埋了巴汰的疯闹惹激了,青色的脸变成紫色,大声地批评我们,“出没于——大街小巷,何谈于——理想”那时我们都笑了,第一次听到如此抑扬顿挫、之乎者也的批评。从此,这句话便成了班里的流行语,不管是谁扮着鬼脸一说,便会引起全班的哄堂大笑。回家后,告诉家长,家长也都禁不住笑。那时的王建峰还没有对象,显然村子里的姑娘都不行了,主观上他看不上,客观上也没有岁数那么相当的了。他是“大学漏子”,似乎错过了村里人娶媳妇的花季。王老师经常会到我家串门。每次来,父亲和母亲都热情地把王老师让进屋,毕恭毕敬地倒茶。在父母眼里,他不是村里人,他是文化人,是先生。如果有时间,还会留下来吃饭喝酒,一盘花生米,一盘土豆丝,父亲和王老师便能唠上半宿。对于老师到来,我既兴奋又紧张,不敢进屋,就在外屋和门后,听他们扯东扯西地聊,全是国家大事,没有切近的过日子的话。听得很新奇,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一次王老师来我家,正赶上立春日,母亲便拿出一块青萝卜切成小片,大家一人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是为“咬春”。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每个人似乎依然快乐。小学毕业后,我便到了三合乡念初中。大约是初二吧,王建峰老师居然也转到了三合乡中学工作,记得是教授地理或自然学科。见面很是惊喜,我到他的办公室看他,办公室有五六个人,白天一起工作,到了晚上,王老师就住在这间教研室,一张单人床,自己烧炉子。从此放学后我便经常跑到他办公室,他备他的课,我做我的作业。有天晚上他要出去办事,大概是出去吃饭吧,很晚没有回来。我做完作业就躺在他床上,不知道啥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发现睡在王老师的床上。王老师一边叠着被子一边说,“看你睡着了,也没招呼你,我就搭个边儿”。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初中还没毕业,王老师就离开学校了。具体什么时候走的、什么原因、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一个叫“窝棚”的地方,几乎不回林齐岛屯里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老师也没回屯里。等到我上中专后,我家又搬回到林齐岛。有一次我放假在家,王老师居然来我家了。这次,他是来抓猪的。他和一个陌生人,熟练地把我家的猪按倒,然后捆上绳子抬到车上,急忙就离开了。看着王老师风风火火的背景,我一时还回不过神来。记忆里那个张嘴之乎者也的老师,怎么也难以与眼前这个“猪贩子”重合起来。从此便失去了联系。有时可以听到些零零碎碎的消息,比如他在大连他弟弟那里生活,他结婚了,等等。但都是碎片。再后来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