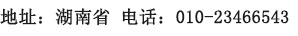我的姥娘叫郭陈氏,如果健在的话现在95岁了,旧社会男女是不平等的,所以女人没有名字。
姥娘来到我姥爷家时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那时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娃娃亲”。
这种婚姻都是基于双方家长对于对方祖辈的家庭、家风、人品等各方面的了解和考量来确定一门婚事。
我姥娘中等个头,身材清瘦,总是在脑后把头发挽成一团然后套上一个网,形成一个球。
我的姥娘是个典型的小脚老太太,我小时候总能看到姥娘用一块挺长的白布带裹脚。
听姥娘说小时候裹脚是慢慢来的,一点一点地裹成这个样子的。连个名字都没有,也就没上过学。
我的姥娘生在山东长在山东,随垦荒团来东北时大约35岁了。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深,所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思想早已深深根植在姥娘的灵魂中。
我姥娘从来不说过激的话,从不做过分的事,从来没见过姥娘发过火。
稳重大方、贤惠善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任劳任怨……这些东方女性的美德无不集中体现在我姥娘身上。
我们的老家莱芜市羊里镇距离泰山仅几十里路,而泰山又是儒释道融合的圣地。
所以我的姥娘非常信仰“积德行善”“好人好报”;同时又相信“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凡事讲究忍让三分,从不与人争,更不与事争。
虽然我的姥娘没有文化,但我小的时候姥娘给我讲了好多聊斋的故事,大都是疾恶好善、因果报应之类的内容,儿时的我听得津津有味。
这些故事在我后来的成长和学习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后来爱好文学和从事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对儿童通过故事进行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这在许多人身上都得到了验证。
姥娘不只是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对我家的帮助也是非常多的。小时候我母亲因为眼疾去大庆住院治疗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妹妹还小,只好被父母带在身边。我们兄弟三人当时在家,我大哥当时能有十岁的样子,我大概七八岁,我弟弟也就五六岁。
我姥娘就在家照顾我们,当时正是冬季,姥娘忙里忙外,喂猪喂鸡,打水、抱柴禾、做饭,忙得一天不着闲。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就干些力所能及的活。
我也学着灌暖壶,抱柴禾。有一回我端着一个刚灌满的暖壶往里屋走时,不小心被柴禾绊倒了,不过我坚持举着暖壶,真是万幸――没烫着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天晚上姥娘说得去粮食加工点粉一些苞米做饲料,我们兄弟三人和邻居家的小伙伴杨光明、郭增新一起用木爬犁拉着半麻袋苞米往加工点拉,当时地上也没有雪,只能在干地上拉爬犁,所以格外的沉。
我家到加工点只有五十多米的距离,结果我们几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整整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给运到地方,而且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第二年,我妹妹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而肌肉感染,险些丢掉性命,医院给妹妹治病。
这一次也是我姥娘在家照顾我们兄弟三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雪挺大。我上一年级了,对姥娘的帮助也就少了。里里外外,喂猪喂鸡,这些活把我姥娘累得够戗。
姥娘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小时候姥娘在哄我们的时候经常就地取材,给我们制作一些小玩具,非常好玩。
见到高粱莛子,姥娘取一节莛子,把外边的硬皮一条一条地扒开拽掉,再把每一条篾子的两头扎进穰子里,好像一个灯笼的骨架,又像一个圆圆的西瓜。
放在地上,在春风的吹动下滚动着,它欢快地舞动着轻盈的身姿奔向远方,特别有趣。
姥娘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总是遵从“施惠勿念,受恩莫忘”的理念,见贫苦亲邻总是尽力帮助。
虽然自家也很贫穷,但总能与别人共渡难关。亲友邻居,谁家有困难的时候,我姥娘总是热情相助。加上姥娘为人谦和,从不计较得失,所以跟亲戚、邻居、朋友相处都非常融洽,交情深厚。
从山东老家移民东北时,周围的亲友和邻居听说以后舍不得让姥娘一家走,都极力劝阻。
可是当时在山东资源少人口多,一家五口人没法生活下去,只好随垦荒团闯东北,看能不能闯出一条生路。姥娘和姥爷经过商议只好带着行囊选择夜间出发了,要不白天就走不了,这些亲戚和邻居是不可能让姥娘一家走出去的。
后来的几年当中经常有山东的老乡在东北生活不习惯就搬回去了。
每当这个时候,姥娘在老家的好姐妹和婶子大娘就到村头翘首以盼,盼望着姥娘一家也能像他们那样搬回山东老家,她们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一次次她们得到的只有以泪洗面、大失所望和怅然若失,并未见到姥娘一家的归来。
她们到死也没等到那一天,姥娘自从来到东北就再也没回去过。她们从开始的“生离”到头来真的成了“死别”。
想写信,她们都没有文化;想邮照片,当时又没有那个条件。我想,在九泉之下她们一定圆了这个梦了吧?
姥娘是个极有头脑的人,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缝缝补补,不管什么东西,在姥娘的手里都是有用的,不能让它白白浪费了。
干什么活都能有条不紊、有理有据。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极贫乏的,天天粗粮能接上流就不错了。
我姥娘在贫困的条件下总能利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最好吃的饭食。我姥娘就到地里采些野菜来,比如:苋菜、白蒿、苣荬菜、婆婆丁……这是在关里时就练就的功夫,什么野菜能吃早就认识了。
我记得小时候姥娘用做豆腐的废料――豆腐渣,加上白菜一炖,特别好吃;夏天的时候就用苋菜炖豆腐渣,也非常可口。
夏天的时候南瓜蔓打叉子扔掉的空心蔓儿,姥娘也舍不得扔,把外边带刺的皮扒掉,切成段用豆油一炒,吃起来香脆可口,绝对一道美食。
到了秋天,房前屋后的香蒿成熟的时候,到处散发着香气。姥娘就采下来,跟豆腐一起发酵,做成“丝闹豆腐”,也非常好吃。
为了能家里人吃的好一些,姥娘坚持天天泡苞米面,推磨,摊煎饼。这种粗粮细做是很辛苦的,也是很劳累的。我小时候经常帮大人推磨,这个活儿绝对能考验一个人的耐力,也是一种磨练一个人坚强意志的好方法。
一圈一圈没完没了地推,直到彻底把一水桶煎饼糊子全部推完,这时你才能高兴地长出一口气,伸伸懒腰,舒展一下腰身。
要想摊煎饼,推磨是很劳累的一关。而在鏊子跟前摊煎饼又是很遭罪的活儿,上边的蒸气熏着,下边灶堂的火烤着,又要不停地忙碌,所以辛苦是肯定的。
现在的人们都已经不摊煎饼了,也不需要摊煎饼了,更主要的是吃不了那份苦了。
旧社会大男子主义盛行,我姥爷也不例外。我姥爷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我姥娘和孩子,也不管大事小事就耍威风。
不管什么活,只要妇女和孩子能干的活就让我姥娘和孩子去干,有什么好吃的反而我姥爷优先,我姥娘和孩子得等他吃完后才能吃。
我姥娘则不然,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先给别人吃。我姥娘经常说一句话:“别人吃了传名,自己吃了填坑。”
这一句话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听姥娘说即使是在坐月子时她也得去外边抱柴禾,刮大风时也要去外边找重一些的东西把柴禾垛压住,以防大风把柴禾垛给掀翻了。
推独轮车,扬场,筛筛子,簸粮食,这些男人干的活我姥娘都干过。每当姥娘受委屈时她总是忍辱负重、波澜不惊、任劳任怨。
在年我顺利考上泰来师范学校,我动身去上学的时候,姥娘和姥爷都来为我送行,他们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转眼到了寒假,我回家后放下行李就要去看望姥娘和姥爷。这时母亲突然喊了一声:“你先别去你姥娘家了,你姥娘已经去世了!家里怕耽误你上学,再说你姥娘去世太突然了,就没告诉你。”
这时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像被钉住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这句话对于我来讲就像晴空万里中的一声炸雷,当时使我目瞪口呆,老半天缓不过神来。
我心里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上学走的时候姥娘不是好好的吗?母亲告诉我,在11月份我姥娘得了急病,在家治了几天等待好转,没想到不几天就去世了。
听了母亲的介绍以后我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怎么也喘不过气来。我呆若木鸡地坐在凳子上静静地哭泣着。随着滴滴泪水的滑落,姥娘的音容笑貌就像幻灯片一样快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内心里真是倒海翻江,心如刀绞。
没想到,那次姥娘送我上师范竟成了永别!谁都无力挽留一个人的生命,我只能祝愿我的姥娘在九泉之下――“溜溜的宝马,足足的盘缠;甜处安身,苦处花钱。”
姥娘去世后好多年以后,姥娘生前的好姐妹和婶子大娘还经常念叨我的姥娘。
她们有时感觉我的姥娘那熟悉的身影又迈着蹒跚的脚步,从院子前边朝着她们的大门走来……一个人在去世多年后还能被人经常想起来,经常被人纪念,那么这个人也就算“不白活一回”了。
后来,姥娘去世后唯一的一张照片也在我家给弄没了,这成了我一个永远的心结,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在年7月份我和爱人回山东老家探亲时,我们出于对我姥娘的缅怀特意去了姥娘的老家――羊里镇郭王石村,顶着38度的高温走访看望了我姥爷的族人。
虽然我们双方相互之间从未联系,也未曾谋面,但亲戚们对我们非常热情,真正把我们当作一家人看待。
其实,从血统上来讲我们就是一家人啊!从中我们收获了满满的亲情。
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有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最重要的一个人,而对我来讲这个人就是我的姥娘。
姥娘的思想影响了我的一生,姥娘的精神鼓舞着我奋力前行,姥娘的一言一行无不教育着我遵从中华传统美德去发展壮大自己。
著名诗人臧克家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有的人》中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我的姥娘虽然已经归天快四十年了,她老人家留给我的记忆有些已经渐渐模糊,但姥娘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就像刻入石头的字一样深远。
姥娘虽然已经仙逝,但她老人家却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姥娘的名字并没有刻入石头,但却“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作者简介:张智修,林甸县花园镇中心小学火箭分校教师,年毕业于泰来师范学校,大专学历,文学爱好者,林甸县作家协会会员,参加工作以来发表文学作品和专业论文几十篇,荣获各类奖励几十项。教过的学生中有九个攻读了硕士研究生,有四个攻读了博士研究生。
林甸往事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