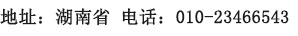题记:
跨年的最后一天,也许只有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会勾起对往事的追忆。那些幼时生动的画面满脑满眼,一张张面孔既熟悉又陌生。此刻,突然发现大半生有太多的似曾相识关于月夜雷同的场景,曾经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竟然一股脑地在脑海里深处喷涌而出。在我记忆中,乡村老家的月夜魅力是独有的,也许只有走在孤独的路上更让人浮想联翩。小城故事的月夜诉说人生打拼的章节,就连标点符号都是那么的在意。乡村老家的月夜有独特的魅力,还有冬天皑皑白雪,万家灯火,又增添多少童年的回忆。我的祖辈生活在齐鲁大地,少年时短短的三年在祖籍之地,更是在梦中还在呼唤祖母,那是放夜校时,十一二岁的年纪,在我祖辈留下的用石头砌成石头院子,也许就是恐惧,其实就是恐惧后面有妖魔鬼怪,每每进院的大门,一路喊着一路奔跑着,瞬间见到祖母在油灯下摇着纺车,彼时已经是四十年前的片段。眼睛好像模糊不清,外面的冷气迅速就想给睫毛冻上冰。最快乐还是夏天依偎在祖母身边,望着美丽的星空,听祖母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每个星星祖母都能讲出故事。蛙声,知了声,还有讲不出小虫子声音!石墙上小壁虎趴着寻找蚊虫,蝙蝠飞来飞去。祖母说,蝙蝠是老鼠偷吃了盐变的。后来在初中学了生物才知道祖母讲的是传说!月夜还是让人更清醒,也就是在新冠疫情时看大门的保安常说的三句话,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哲学家研究的道理走向最基层。也许就是大道至简、大智若愚吧。
四
在老家放寒假也算是开心的了,最起码跟着祖父或者小姑去走亲戚。平时食物就是地瓜,偶尔吃一顿玉米面的窝窝头算作美食。
上夜校时,放学回到家肚子饿,把祖母摊的煎饼拿一张,是玉米面和地瓜面混合面的,祖母有个老式油罐子,从里拿出小勺滴到碗里几滴,倒上开水,放几粒咸盐,把煎饼掰碎泡到碗里,饥肠辘辘,吃起来津津有味。就算过年的饺子也掺了地瓜面的。
只有走亲戚才真正吃上一顿白面馍馍。那时走亲戚特别好玩,在提篮里放上几斤白面馍,也不记得放其他什么东西了。
跟着祖父去过我姨家,东平尹山庄。比去祖母的娘家还要远,我跟着祖父走山路,从山路走没感到害怕,只是好奇。
那年好像过了麦,老家那里年后或者收完麦走亲戚,就像东北的串门。走过一座又一座山,山上怪石嶙峋,树木丛生。老家的蝈蝈特逗,吱吱吱,非常好捉,在草丛里草叶上,只要想抓就能抓住,它的身子有点胖。
东北的蝈蝈叫声又响又长,吱——,它身体瘦小,而且特别敏感,有点动静飞的无影无踪,很难捉。
沿着崎岖石路,对于山我还是好奇询问着祖父,这个叫什么名字,那座山叫什么名字,路过一个窄的山口地方,祖父告诉我这里叫杀人桥子,没有桥,只不过是一个山口,回来时走到那里就浑身发瘆起来。
祖父说从前这里有劫道的,有一次劫道把人杀了。边走祖父告诉我那个山,高高的,像一个人圆脑袋叫牙山,依稀看到山顶上有日本人修的炮楼山的西侧,有非常陡峭的山路,模糊看到上山台阶。
老家是革命根据地,祖父当年是村里救助队,帮助八路军后勤抬担架。他还讲了好多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事迹。
还有油山、五埠等,听说现在都保护起来了,成了纪念馆,拍抗日神剧都在那里拍,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
老家邻居有个叫小五的,星期天我跟着他去割草,背着筐,割满筐了背回去交给队里的牛棚。
牛棚里放着一排排石头槽子。牛棚负责过秤的是近门五大爷,他是祖父二哥家的大儿子,他比父亲大,他做事特别认真。
后来就看到队部墙上有我的名字和交草累计数。说是可以换工分,也不知最后给没给,我还给祖母说,我不是黑户了,还能给家挣工分了。
小五我喊他五哥,他是祖母前院的邻居家的孩子,比我年长两岁,他特别好玩,割草累了,他就找到一个小蜗牛,用手捏着着蜗牛就念,几乎贴到脸上,眼睛虔诚几乎不眨的念道,小蜗牛,先出角后出头。
我感觉他念了快一百遍了。
小蜗牛真的从里面爬出来了,我感到特别好奇,是小蜗牛听懂话了,还是小蜗牛出来透气呀。
院子里臭椿树与椿树也不一样,椿芽长的不高,叶子刚发出来,叫春芽,用带钩子的长杆勾住树叶掰下来,用盐揉了当咸菜吃,也能到年用春芽炸着吃。
臭椿就不一样,它长的又粗又高,树叶都臭,可是在树上有臭树牛,有两厘米那么长,尖尖的嘴特别硬,有时候它装死,拿着它在石头上磨它的嘴,咋磨它也不醒,可好玩了。
院子墙中间那里有一棵枣树,枣树枝条也都是刺,并且每当树上结满果子时,毛毛虫也满满的,绿绿的虫子,一爬一躬身,浑身都是毛,如果扎了身上特别疼,我胆小从来都是躲着它。
到七月份,被风刮下来的枣洗洗就吃,又脆又甜,但不能吃多,吃多会胃疼。
有时我把枣放到祖父烧的炉子炉箅子下烤,又甜又面吃多也不会难受,也许是我的独创吧。祖母说,到八月十五才打红枣呢!
林甸往事公众